更多
分享

在許多國家「性替身療法」(surrogate sex therapy)充滿爭議且未被廣泛實施,爭議是要僱用一個人充當患者的性伴侶。但在以色列,政府出資為那些受過重傷、需要性康復的士兵提供這種治療。
以色列性治療師羅尼特·阿洛尼(Ronit Aloni)的特拉維夫諮詢室看起來和你想象的差不多。這裏有一張舒適的小沙發供客戶使用,還有她向客戶做解釋時需要用到的男女性生殖器圖。
但在隔壁房間發生的事更令人驚訝,這裏有一張沙發牀和蠟燭。這裏是性代理伴侶(也譯:替身性伴侶)(surrogate partners)幫忙教導阿洛尼的一些客戶建立親密關係並最終發生性關係的場所。
「它看起來不像酒店。更像一棟房子,像一間公寓,」阿洛尼說。這裏有一張牀,一台CD機,和一個牆上還裝飾著色情藝術品的浴室。
「通常性治療都是夫妻治療,如果沒有伴侶,那就無法完成這個過程,」她繼續說道,「男、女性代理人幫助扮演(治療過程中所需的)夫妻角色。」
雖然批評者將其比作賣淫,但在以色列這種做法已被接受,以至於以色列從國家層面為性能力受影響的受傷士兵付費治療。
「人們需要感覺到他們可以取悅別人,他們可以從別人那裏獲得快樂,」擁有性康復博士學位的阿洛尼說,「人們來接受治療,不是為了尋歡而來,治療過程中沒有任何類似於賣淫的地方。」她堅定地補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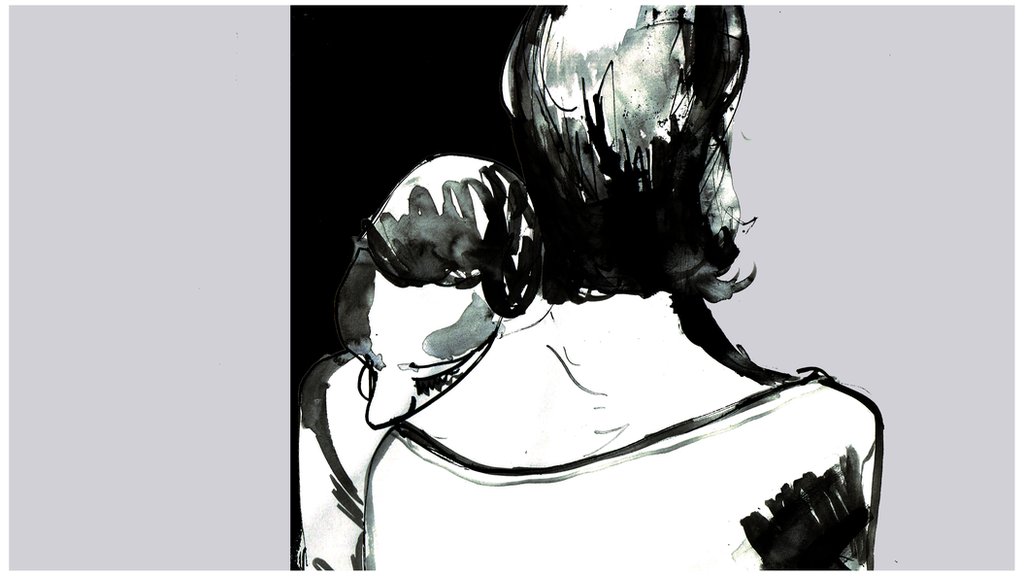
「另外85%的療程都是(關於)親密關係、觸摸、給予、接受和溝通。這些是關於學習成為一個人和如何與其他人產生聯結的方式。到建立包含性關係的兩性關係時,治療過程就結束了。」
希望被稱為A先生的受訪者表示,他是以色列國防部第一批為替身性療法買單的士兵之一。約30年前,他還是一名預備役軍人時,遭遇一場改變生活的事故。一次高空墜落使他腰部以下部位癱瘓,導致他無法像以前那樣進行性生活。
「受傷後,我列了一個『待做事項清單』」,他說。「我必須(能)自己洗澡,自己吃飯、穿衣,自己開車,獨立做愛。」
A先生已結婚並育有小孩,但他的妻子不願意與醫生和治療師談論性問題,所以她鼓勵他向阿洛尼求助。
他分享阿洛尼如何在每次治療前後向他和性代理人提供指導和反饋的情形。
「從頭開始:撫摸這裏,撫摸那裏,然後一步步,直到最後獲得高潮。」他說。

A先生認為以色列為其每周的療程付費是正確做法,就像為他的其它康復治療付費一樣。如今三個月的治療費用為5400美元。
「我的生活本意不是去找性代理人。但好吧,我受傷了,我想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康復。」他坐在輪椅上,穿著運動服,在去打乒乓球的路上說。
「我沒有愛上我的性代理人。我結婚了,只是為了學習達到某個目標的技術。我把它當成一件很合理但又必須要做的事。」
他指責西方對性的隨意態度給「替身性治療」帶來誤解。
「性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對生活的滿足感,」他說,「這並不意味著我風流成性,不是這樣的。」
在阿洛尼的診所裏,不斷有不同年齡和背景的人謹慎地拜訪她。
許多人因為親密關係問題或焦慮或遭受過性虐待而難以擁有一段浪漫關係。其他人則有身體和心理健康問題。
阿洛尼從她的職業生涯初期就特別關注殘疾客戶。她的幾位近親都有殘疾,這其中包括她的飛行員父親。一次飛機失事後,他腦部受傷。
「我的一生都與那些不得不面對和克服不同殘疾的人很親近,」她說,「這些人都得到很好康復,所以我有非常樂觀的態度。」
阿洛尼在紐約學習期間與一位從事殘疾人工作的代理人關係密切。
當她在20世紀80年代末回到以色列時,她獲得了猶太教祭司對使用性代理人的認可,並開始在一個農村社區的康復中心提供治療。
但猶太教祭司有一條規定:已婚男子或已婚女性不能做性代理人,阿洛尼一直遵循著這條規定。
隨著時間推移,她贏得以色列當局支持。在她的診所接受過替代性治療的大約1000人中,有幾十位是受傷的退伍軍人。許多人有腦外傷或脊髓損傷,他們的治療由國家資助。
阿洛尼認為,以色列以家庭為中心的文化及對武裝部隊的態度對她有利。大多數以色列人在18歲時就會被徵召服兵役,他們可以作為預備役士兵一直服役到中年。
「自建國以來,我們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她說,「在以色列,每個人都認識受傷或死亡的人,大家都有積極的方法來補償這些人。我們覺得對他們有義務。」
一位40歲左右的高個子男人正坐在以色列中部的一個花園裏,他腿上蓋著一條毯子。他是一名前預備役士兵,他的生活在2006年的黎巴嫩戰爭中被打碎。
我們姑且稱他為「大衛」,他無法說話或移動。

他只能在職業治療師的幫助下進行交流,如果她支撐著他的手臂,幫他拿筆,他就能在白板上寫字。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剛從遠東回來。我念過大學,當過酒吧老闆。我以前喜歡運動,喜歡和朋友在一起。」大衛說。
他所在的部隊受到攻擊,他的腿部和頭部嚴重受傷,並住院三年。他說那段時間他失去了生存意志。
在職業治療師建議進行替身性治療後,情況才開始好轉。
「剛開始進行替身性治療時,我覺得自己像個什麼都不是的失敗者。在治療中我開始覺得自己是個年輕又帥氣的男人。」大衛說,「這是我受傷後第一次有這種感覺。它給我力量和希望。」
大衛明知道這段親密關係必須結束,卻還是選擇開始。那麼他是否有可能在感情上受傷?
「最初對我來說很困難,因為我希望性代理人只屬於我自己,」他說,「但我意識到,即使我們不是性伴侶,我們仍然是好朋友。而且它是值得的。這所有的都值得。它只是幫你重新建立自信。」
雖然通常規定性代理人和客戶不能在治療之外保持聯繫,但大衛和他的性代理人——一位化名為塞拉菲娜(Seraphina)的女性——得到了阿洛尼醫生診所的特別許可,他們治療結束後可以保持聯繫。
自接受治療以來,與大衛關係親近的人說他們看到了他的轉變。他一直專注於計劃未來。
雖然維持性生活仍非常困難,但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他已在護理人員的幫助下外出,開始進行更多社交活動。
塞拉菲娜與阿洛尼的診所合作做性代理人已逾十年。她身材苗條,留波波頭,熱情而又善於表達。
最近她出版一本描寫其經歷的書:《不止是性愛代理人》(More than a Sex Surrogate),出版商稱其為「一本關於親密關係、秘密和我們愛的方式的獨特回憶錄」。
和特拉維夫診所的所有性代理伙伴一樣,塞拉菲娜也有另一份工作。她的工作是在藝術領域。她說,出於利他主義的原因才擔任這個角色。
「所有那些(表面)受苦的人,都有這些一直伴隨他們的隱藏秘密,我真的想幫他們,因為我有能力,」她解釋說。
「我對在治療過程中使用性行為或使用我的身體或觸摸我的身體的行為沒有意見。而且這個主題和性對我很有吸引力。」
塞拉菲娜形容自己「就像導遊」,帶客戶踏上一段她知道前路的旅程。
她已與大約40名客戶合作過,其中包括另一名士兵,但她說,大衛的傷勢嚴重給她帶來獨特挑戰。她學會幫他寫作,以便他們可以私下聊天。
「大衛是有史以來最極端的案例。這就像在沙漠中行走一樣,你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她說。
「我必須非常非常有創意,因為他根本不能動。我移動他的身體,就像我想象的那樣,如果他能移動的話。他能感受到身體有知覺,但不能移動它。他總是說:『即使我什麼也不說,她很清楚我想要什麼』。這很讓人受寵若驚。」
在做性代理人時,與塞拉菲娜交往過的男朋友們接受她的工作。但她認識的其他女性和男性為了個人伴侶或結婚雲隱而不再做性代理人。
她解釋說,在與客戶親密接觸後向他們說再見是必要的,但可能很困難。
「我說這就像去度假一樣。我們有機會在短時間內擁有一段美好關係,我們應該抓住還是放棄它?這是任何人都能擁有的最幸福的分手。分手理由很美好。我有時會哭,但同時我也很開心。」
「當聽到有人談戀愛、生小孩或結婚時,我無法想象自己的工作有多麼幸福、激動和感恩。」
傍晚時分阿洛尼還在工作,在給一群來自歐洲和遠在南美的性學家做在線講座。
她講述了一些案例,並引用一些研究結果表明,性代理在治療性問題上比經典的心理治療更有效。

她告訴他們:「那些已經和性代理人合作過的治療師都表示會再做一次,這是最有趣的。」
隨著現代外科手術能幫助更多重傷士兵存活下來,她相信替代性治療可以得到更廣泛應用。
「如果不恢復一個人的自尊心,不恢復他們對自己是男人還是女人的看法,你就不能讓他們康復。」她說。
「不能忽視生活中的這一部分。它非常重要和強大。它是我們人格的中心。而且不能只談性。性是一種動態的東西,是我們和其他人之間(產生連結)必須(擁有的)東西。」
在阿洛尼看來,現代社會已對性形成不健康的態度。「我們知道如何拿性開玩笑,如何羞辱別人,如何對性愛非常保守或過於極端,」她說。
「它從來沒有被真正平衡過。從來沒有以應有的方式融入生活,而性行為就是生活。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是本性!」
圖像來源:Katie Horw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