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
分享

▲《平常心》劇作者拉里·克萊默是美國同性戀群體中最早公開呼籲社會公眾、醫療界和政府重視愛滋病疫情的人之一,也為此被紐約同性戀群體列入不受歡迎者名單。(圖/GETTY IMAGES)
三十五年前,一種人們前所未聞的致命病毒在美國東西海岸悄然但迅速地傳播,很快釀成一場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流行疫情。這種病毒一開始沒有正式名字,相當長時間裏大家都叫它「同性戀病毒」、「同性戀癌」。疫情爆發後,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的共和黨政府漠然,社會公眾心態冷漠,對患者更多的是偏見和躲避。後來,這種病被正式命名為愛滋病,而疫情已經從紐約和舊金山的男同性戀群體擴散到世界,在全球流行。
因為愛滋病毒最早在男同性戀群體開始傳播,而政府和公眾無動於衷,所以這個群體最早出現自助自救行動,後來被統稱為愛滋病文學的虛構和非虛構作品也開始出現。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舞台劇作之一是拉里·克萊默(Larry Kramer)的《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又譯《常人之心》)。
克雷默2020年5月去世。
這是一部半自傳體式的舞台劇,展示愛滋疫情爆發後,美國社會、個人、政府和醫療界對這種完全陌生的病毒的反應。當時,大部分人對這種致命的新病毒一無所知,而它開始大範圍傳播時,人們大多以冷漠和歧視的心態面對。劇作者克萊默希望通過這部戲喚起社會對艾滋病毒的重視,打破冷漠。
值得一提的是,毒品注射在愛滋病毒的傳播中所起的作用,在許多艾滋文學作品和評論中較少著重墨敘述;早期作品的側重點是同性戀。
時間快進到2019/2020年,又一種新的病毒爆發全球大流行,美國迅速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傑克·金(Jack King)重溫當年那出《平常心》的振聾發聵之力。
1981年7月,紐約和加裏福尼亞的男同性戀人群中發現26宗卡波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病例;那是一種非常罕見的腫瘤。在此之前大約一周,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發佈了一份報告,陳述了5名身體健康的同性戀男子確診得了肺囊蟲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導致這些機會性感染的元兇是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又稱愛滋病毒,因為感染了這種病毒而患的疾病被稱作愛滋病(AIDS,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愛滋病毒會摧毀人體的免疫系統,使人對病菌喪失抵抗力。
從1970年代早期開始,HIV就在美國同性戀群體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大肆傳播。這跟男同性戀群體中濫交現象普遍有關,而性行為不受任何形式的約束,又跟1969年石牆騷亂(Stonewall rebellion)有關;那次事件之後,濫交不僅是一種非常規社交風俗,更成了一種革命性的行為。
1981到1987年間確診的愛滋病患者後來全部病逝。舊金山一位名叫保羅·沃爾伯丁(Paul Volberding)的醫生參與了美國第一個愛滋病人住院病房的設立。他2016年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回憶:「那是當時最致命的病毒感染疾病。如果不治療,98%的患者必死無疑。它比埃博拉病毒、比天花都更厲害。」
不過,正因為這種病毒前所未見,美國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到1982年9月24日才開始使用Aids這個縮寫作為疾病的名稱。在那之前,醫務人員一般都把這個病毒叫做Grid,意思是與同性戀相關的免疫缺陷,或者乾脆就叫「同性戀癌」、「同性戀鼠疫」。這些稱呼隱含的一層意思是只有同性戀者才會得這個病。
按照正常邏輯,其實不難理解病毒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沒有歧視。但是,當時美國是里根總統主政,社會思潮傾向於保守主義,因此,右翼團體、比如里根政府的盟友,傑裏·福威爾(Jerry Falwell)的道德多數派,不失時機地把艾滋病當作用來攻擊對手的理想彈藥。
福威爾聲稱愛滋病是「上帝的憤怒」。這個說法在社會上流傳廣泛。1988年,劇作家威廉·霍夫曼(William H Hoffman )把愛滋病流行跟二戰中猶太人大屠殺作類比,「和今天的現狀一樣,公眾對受害者的態度是害怕、仇恨和漠然交織的混合體。」
面對這種社會偏見,藝術界開始反彈。在陸續湧現的作品中,最有力的是拉里·克萊默的舞台劇《平常的心》(The Normal Heart,又譯平常心、常人之心),1985年在紐約公演。劇情圍繞美國第一所艾滋病救助診所成立初期掙扎求存的狀況。這個診所是1982年克萊默與他人共同創辦的。
克萊默(1935-2020)的編劇生涯從好萊塢電影劇本創作開始,後來轉到舞台劇創作。他一輩子從來沒有把自己看作同性戀權益活動分子。他1978年出版的小說《Faggots》,對同性戀社區的濫交風氣大加貶斥,結果從1980年代初就被紐約的同性戀社區列入不受歡迎者黑名單。
但是,克萊默堅持己見,認為這個世界亟需警鐘、行動號角,而這正是他可以提供的。

2000年,克萊默兩個劇本的合輯出版,美國劇作家托尼·庫什納(Tony Kushner)在序言中寫道:「這兩個劇本合在一起,令人信服地展現了一個關鍵而可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一個致力於擺脫長達數百年的迫害和壓迫的新興社區在政治和文化層面達到了一些最重要的目標,而又恰恰在這個關鍵時刻被蒙蔽了雙眼,蒙蔽它的,是與這個世界誅心的冷漠及赤裸裸、或略加掩飾的仇恨悲慘地連在一起的生物學領域的恐怖。」
庫什納本人亦已成為美國愛滋危機文學經典的另一個代表人物,這段文字是他發表的重要評論 — 讀庫什納的分析就意味著不但對《平常心》的精神遺產有足夠的理解,對它背後灼熱的意圖也一樣。
這是以藝術面目出現的政治,誕生於一場正在醞釀的危機的熾熱餘燼,那場危機的爆發導致70萬美國人喪生,其中絶大多數來自同性戀者和非裔社區;自那以來,全球艾滋病死亡人數達到3300萬人。
用庫什納的話表述,克萊默寫《平常心》是為了借此「催化他的社會發生巨變」。他繼續說:「我們都知道,那件事現代戲劇早已無能為力,也有罕見的例外,比如拉里·克萊默創作《平常心》。」
這是一部基於真人真事但隱匿姓名的影射作品,劇中的主要角色,奈德·維克斯(Ned Weeks)就是略加掩飾的克萊默本人。《平常心》從一群同性戀權益活動組織成員的角度再現了北美愛滋危機爆發前後那幾年的人和事,講述了當時在政界精英對危機無動於衷的情況下,這些權益活動人士自發成立了同性戀愛滋救助機構GMHC(Gay Men's Health Crisis)的經歷。
作品行文冷峻無情、平鋪直敘,基本上沒有隱喻和詩意,充滿了正義的憤怒;年復一年,越來越多的人被這種疾病奪走生命,而奈德和他的同伴們認為政治精英和整個社會都對這種惡疾視若罔聞,漠不關心。
克萊默描述的一代男同性戀遭受的苦難,使得美國看上去就像戰場,不少愛滋病患者死後得不到死亡證,屍體塞進特大號垃圾袋扔一邊沒人管;較幸運的則被親友送去安葬,這類葬禮之頻繁幾乎成了一種社交活動。
愛滋文學領域另一位著名編劇,克雷格·盧卡斯(Craig Lucas)在《平常心》公演前一年就看過演出了。他是1989年一部同性戀題材的影片《愛是生死相許》(Longtime Companion)的編劇。
盧卡斯對BBC Culture 回憶當時的情況說:「那時這部劇已經在一些非盈利劇場輪流上演,看過的人都說那是一部阿吉普特(政治宣傳活報劇),不是真正的舞台劇。」
盧卡斯的伴侶蒂姆1984年在紐約醫院接受總住院醫師的培訓,目睹了愛滋感染病例驟增,然後有一天發現自己也出現了症狀。
盧卡斯記得:「當時我們倆都懵了,心裏充滿焦慮、恐懼,確信自己很快必死無疑。拉里以令人驚奇的激情和力量(與艾滋病)的搏鬥在那部劇中大放異彩;當時它給人的感覺是充滿了震撼人心的生命力,重要非凡,像海嘯一樣席捲了我和其他許多人。」
他說:「在政治上,這齣戲的意義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羅納德·里根總統個人對愛滋病危機的態度長期以來一直是人們議論的話題。那時和現在,許多人認為里根的總統任期就因為他對愛滋疫情應對無效而沾上了一個污點。這是知名傳記作家洛·坎能(Lou Cannon)的看法。今天,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反應遲緩的特朗普政府,也引發了類似的批評。
核心的區別在於,很長一段時間內,愛滋病都被公眾視為同性戀人群的「專利」,不值得同情,因此里根政府並沒有受到公眾壓力,他的政治資本並沒有因為對愛滋病疫情的沉默而受影響。
有傳聞說,里根私下裏還是很同情愛滋病患者的,也有人聲稱他有恐同症,但這些都沒有證據。歷史記錄在案的是,里根身邊有一群心態偏執的人:帕特·布坎南 (Pat Buchanan) 1985年2月至1987年3月任白宮通訊聯絡總監。他1983年在《紐約郵報》評論版撰文說,愛滋病危機是大自然對男同性戀的嚴厲懲罰;白宮新聞秘書拉里·斯比克斯(Larry Speakes)被人稱為「里根時代的公共面孔」,在白宮記者通風會上多次跟記者萊斯特·金索溫(Lester Kinsolving)在愛滋病問題上唇槍舌劍,言辭間透出對後者是同性戀的貶夷。
里根一直到1985年9月17日才正式承認愛滋病流行的爆發;那是在《平常心》公演半年之後。那年年底,美國有12529人死於艾滋病,包括里根的好友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

如果把愛滋危機視為里根總統任期內標誌性事件之一,那就必須把《平常心》視為里根時期美國的標誌性重大辯論之一。
克萊默的箭頭很少直指里根政府本身,而更多是刺向冷漠的政策,這種冷漠在里根總統任內變得系統化、固化,從媒體到紐約市長辦公室,再到社會大眾,無一可赦。
《紐約時報》就被點名抨擊,因為它的報道就像是一些認為事不關己、自己沒有受到威脅的人對疫情輕描淡寫的描述,對深陷危機的群體漠不關心。
《平常心》並非愛滋危機藝術真空中的奇葩。1985年第一部愛滋病題材的劇情片公映,《同伴》(Buddies),第一部直擊愛滋疫情的電視劇《早霜》(An Early Frost)播出,還有威廉·霍夫曼的舞台劇《現狀》(As Is)繼《平常心》之後不久在紐約蘭心大戲院(Lyceum Theatre)登台。
其後幾年,「新酷兒電影運動」興起,除了上面提到的熱內導演的《愛是生死相許》,還有1986年比爾·謝伍德(Bill Sherwood)的《離別秋波》(Parting Glances),托德·海因斯(Todd Haynes)1991年的《毒藥》(Poison) ,還有許多愛滋權益活動藝術家的各種作品湧現。
除了克萊默、霍夫曼和海因斯,當年美國愛滋文學藝術圈裏的其他活躍人士後來陸續都死於愛滋病引發的綜合症。
雖然同時代所有以愛滋危機為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都具有強大的社會衝擊力,克萊默的活力激情無與倫比,《平常心》就像機關炮一樣瞄凖他視為致命的冷漠疏懶的混合體連番噴吐怒火,直擊觀眾靈魂。

這種無雙的威力,部分原因是劇情內容直接來自當時的生活現實。克萊默沒有時間去反思、回顧,不像官方正式承認愛滋疫情爆發10年、20年、30年後的同類題材作品。
《平常心》就像前線戰場上發自洪荒之力的怒嗥,揚起飛沙走石,那種目睹身邊親友死去而感到自己必須採取行動的迫切感令人感同身受。
劇作家馬修·洛佩茲(Matthew Lopez)初次讀到《平常心》劇本時,還在戲劇學校上學,當時「只感到字裏行間灼人的熾熱」,就像文字在燃燒,他最近接受BBC Culture 採訪時回憶。
2004年,這部舞台劇重新上演,在公共大戲院,洛佩茲去看了,證實了自己當年讀劇本時的感受無誤。他說,《平常心》當時是表述愛滋疫情的核心文字,現在依然如此。
劇中主角奈德和他在紐約一家大律師行當律師的親兄弟本對話。本拒絶加入奈德創辦的同性戀愛滋救助機構GMHC的理事會,奈德認為這不僅是對這個機構的不屑,更是對自己同性戀身份的排斥。
本:「聽你說話好像我成了你的敵人。」
奈德:「我開始認為你和你的那個直男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在設法理解為什麼沒人願意聽說我們正在死去,為什麼沒人願意幫一把,為什麼我的親兄弟也不願意幫我一把!」
無疑,這段話是愛滋疫情最初幾年許多受害者的心聲。
洛佩茲解釋說,《平常心》留給後人的遺產「不光是一部戲,還是一段歷史,是一段活歷史」,沒有比它更緊扣現實的了。它講述的是對病毒和政治疏瀆的無休止的抗爭。
他說,人類天性中有一種柔化記憶的本能,隨著時間流逝過去的記憶變得不那麼棱角分明,焦點逐漸模糊。而《平常心》的意義在於它將永遠會把那次危機的真實面目展現在後人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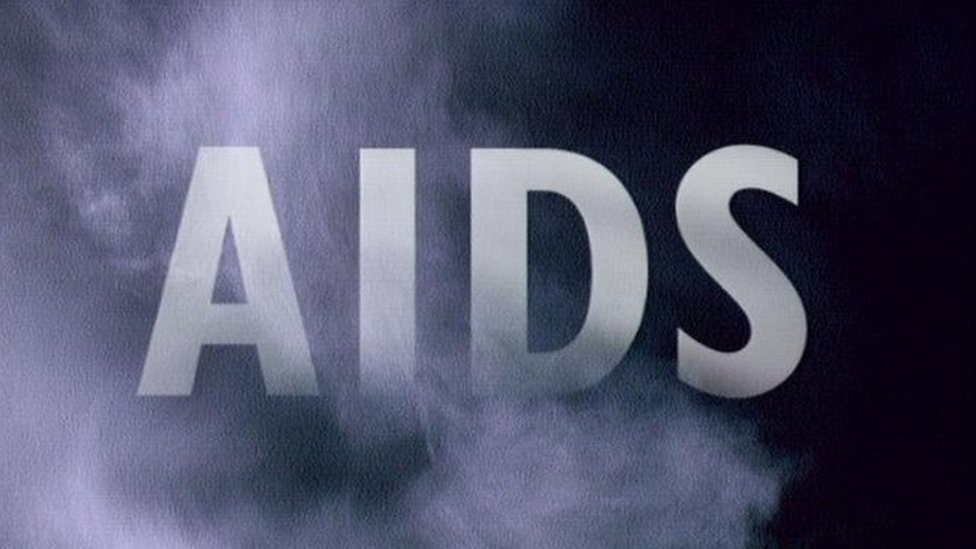
洛佩茲對里根政府面對愛滋疫情的遲緩、冷漠和不作為毫不吝惜批評之辭 ,認為就是政府的不作為導致無數人無謂喪生。
但里根政府的辯護者指出,1989年里根卸任時,美國政府用於愛滋病毒/愛滋病研究和預防的預算金額總計超過23億美元,而且里根本人不止一次強調抗擊愛滋病是政府的要務之一。
克萊默在劇本的題詞中寫道:「《平常心》是我們的歷史。如果不是有那麼多人無謂地死去,就不可能創作這部劇。吸取教訓,繼續戰鬥。讓他們知道,我們是一群特殊的人,突破常規的人。屬於我們的那一天終將到來。」
至少在西方社會,現在的同性戀人群享有的權益和特權可謂空前,但人們的集體意識中關於愛滋病依然是一種致命惡疾的那一部分似乎淡漠了,很少有人注意到,現在每年有1.3萬美國人死於愛滋病,其中很多是美國南方有色族裔男同性戀。
不過,《平常心》今天仍像35年前一樣振聾發聵,今天的讀者仍舊會在劇本的字裏行間感受到克萊默對他眼中的沒有底線的冷漠無情的憤怒,也可能會聯想到那種憤怒是否仍可喚起某種共鳴。
歡迎到BBC Culture 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