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
分享

從藥物引導下的昏迷中醒過來時,西蒙·法瑞爾(Simon Farrell)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試圖扯下自己的氧氣面罩。
他已經在重症監護病房(ICU,深切治療部)裏10天了,依賴一台呼吸機。
「我想要將面罩從我臉上扯下來,然後護士就不停地將它戴回去,」他回憶說。
醫生叫醒他的時候,他的身體剛剛戰勝了最嚴重的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但是他受損的肺還需要氧氣來支持。這個有兩個孩子的46歲父親的譫妄嚴重到一個程度,他想拒絶自己賴以生存的氧氣。
「阻止我試試,」他記得自己這樣說過。當時伯明翰伊麗莎白女王醫院(Queen Elizabeth Hospital)的護士說,如果他不消停的話,他們就會用拳擊手套大小的醫學手套套住他的雙手。
「最後他們不得不用膠帶捆起我的手,我想把手套也扯掉,我咬破了手套,然後他們又套上新手套。」
這對於在重症監護病房裏工作的人來說都不陌生。2019冠狀病毒病對於最嚴重的患者所造成的損傷,令病人使用呼吸機的時間以及鎮靜劑的強度都超過一般的ICU病人。
這會產生「很多的譫妄、迷糊和錯亂的神智」,庫爾萬特·達德瓦爾醫生(Dr Kulwant Dhadwal)說。他是負責倫敦皇家自由醫院(Royal Free Hospital)重症監護部的顧問。
「通常,如果你經過外科手術,或者作為一般的肺炎病人來到重症監護病房,你等他們醒來,他們不會這樣迷糊和錯亂。」
「給這群特定的病人移除呼吸機要難得多。」
即使成功完成這個程序,也只是漫長的身心恢復過程的開始。現在英國已經度過病毒疫情的高峰,無論是醫療系統還是社區,注意力都正在轉向COVID-19患者康復這項重大挑戰。
「康復過程經常被看作一項被忽略的事務,並不是頭等大事,」萊斯特大學的心肺康復科教授薩麗·辛格(Sally Singh)說。
「但是由於冠狀病毒病,以及它所波及的人數,這項需求壓力很大。它成為了全國性的要務——幫助人們復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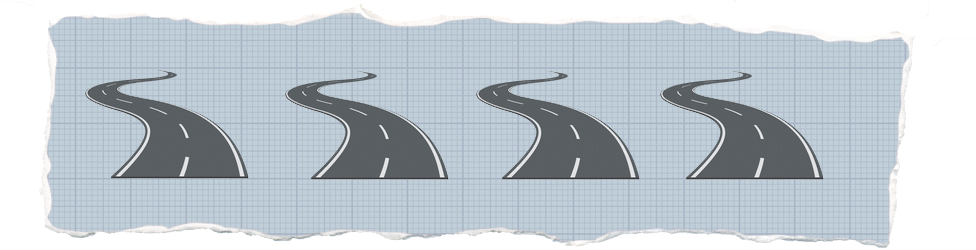
在英國各地,數以萬計的人現正走在這樣一條路上。
在重症監護病房裏,有些人與死亡很近,有些人則不需要那麼多入侵身體的醫療手段來幫助邁過難關。COVID-19令所有這些人的人生發生了改變。
但是,對於重症監護病房裏病得最重的人來說,康復過程在他們從昏迷中醒來之後很久就開始了。身心的支持都必須從一開始就到位。即使在病人睡著的時候,護士和治療者都要幫他們運動關節和身體,來確保他們不會變得僵硬。
「例如,我們有一種牀上的自行車,」普利茅斯國民保健署信託基金大學醫院(University Hospital Plymouth NHS Trust)重症監護病房的專項康復護士凱特·坦塔姆(Kate Tantam)說。
「即使病人在用呼吸機支持多個器官,並且使用多種藥物來維持生命,我們仍然可以讓他們使用自行車。」
「我們將它放到牀上,然後可以將他們的腳放上去,然後機器就會幫你運動了。」
重症監護病房工作人員還會經常對病人說話,在他們深度昏迷的時候告訴他們,現在他們在哪裏,發生了什麼事,還會向他們保證,他們很安全。這些都是為他們醒來的那一刻做凖備。
「有些病人醒來之後會說:『我記得你的聲音,』」達德瓦爾說,「他們會帶著某種記憶醒過來。」

不過,COVID-19的康復過程甚至比一般情況還要更複雜和困難,部分原因是很多ICU病人使用呼吸機器的時間超乎一般地長。
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醒來的時候極度虛弱,儘管有一些人可能會出乎意料地很快恢復體力。
「通常,一個人昏睡了40天或者以上,他們需要六個星期或者更長的時間來徹底脫離呼吸機,才能開始站立或者行走,」庫爾萬特·達德瓦爾說。
「但是這些病人當中有些在一個星期內就有進展了,這是我們覺得很不尋常的,是這種病特有的。」
COVID-19重症初癒時的另一個挑戰是嚴重的炎症。
很多病人受不了呼吸導管插入口中,是因為喉嚨和聲帶上方的部分因為病情而腫脹得很厲害。這意味著醫生經常要進行氣管切開術,在頸部打開一個口,才能找到氣管,找出讓病人與呼吸機連接的管道。
「氣管切開術必須非常注意,它是頸部的創傷術,」雷丁皇家伯克郡醫院(Royal Berkshire Hospital )重症監護病房的顧問卡爾·瓦爾德曼(Carl Waldmann)解釋說。
「所以,令他們脫離呼吸機是一個漫長又緩慢的過程。可能需要一兩個星期甚至更長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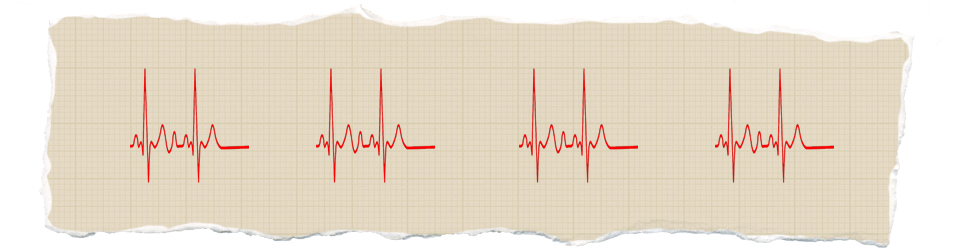
每一個病例背後,都是人的故事。
亞伯拉罕·拉斯金(Abraham Raskin)的家人在4月末被告知,他很可能活不過來了;但在6月12日,他終於從皇家倫敦醫院出院,他在重症監護病房度過了50多天,並且經過一次氣管切開術和一個月的藥物引導昏迷。
「我還活著,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他說,「我差點就完了。」
5月18日護士安排的一次視頻通話,是自4月初入院之後家人第一次看到他的臉。他還不能說話,但是揚了一下眉毛。
亞伯拉罕醒來之後,一度嚴重譫妄。「我說著各種胡話,」他說。
「之後當我聽到自己曾經說過什麼時,我覺得自己是瘋了。這並不令人愉快。」
但現在,他回家了,仍然十分疲倦,而且在進行一個由物理治療師安排的鍛煉計劃。在家人支持下,他晚上能夠上樓睡覺了。
「有些人從這一切當中醒過來之後,連路都走不了,」他說,「還有些人花好幾個月才恢復。我希望自己不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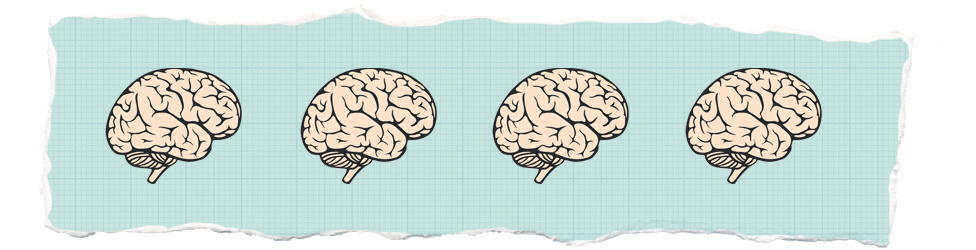
在需要呼吸機器的重症監護病人當中,有多達四分之三會出現譫妄症;而且據很多醫生的觀察,COVID-19的重症病者譫妄症特別嚴重,幻覺也不同尋常地真實生動。
譫妄症可能是因感染本身以及隨之而來的發燒引起,但是為了減少病人痛苦而使用的強力鎮靜劑,以及重症監護室當中令人不安的環境,都會令這種症狀加重。
在病人處於昏迷時,以及蘇醒後開始停藥時,都常常會經歷可怕的幻覺,並會對所發生的一切抱持令人不安的信念。
「譫妄症並沒有像做夢那樣的特徵,」倫敦大學學院醫院(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 in London)的重症監護病房主診心理學家多樂茜·韋德(Dorothy Wade)說,「病人們都是說『它完全是真實的——我是活在這種可怕的平行現實當中。』」
醫生們認為,化學物質的失衡令大腦就身體為什麼不能動彈和病人不能說話而製造出自己的解釋。常見的是人們認為自己被綁架或者虐待,又或者他們認為自己身處監獄裏,即將接受審判。
「他們傾向於覺得護士、醫生以及工作人員全都在策劃一些陰謀,」多樂茜·韋德說,「認為這一切全是陰謀的一部分,為了賺錢而賣掉他們身上的血或者器官。」
這意味著像韋德醫生這樣的心理學家要盡早介入。她說,重要的是不要和譫妄症病人爭辯,而是要試圖安撫,解釋真正發生的事情。
西蒙·法瑞爾在脫離呼吸機之後出院相對快,但是他記得自己經歷的一些譫妄幻覺是非常生動的。
「我記得我的小兒子艾略特(Elliott)穿著防護服走進房間,」他說,「那明顯不對,孩子是不讓進病區的。醫院都被封鎖,那件事沒有發生過。」
不過,在他當時的頭腦中,他相信那是絶對真實的。
「你就是感覺,它就在發生,」他說,「還有一些比這糟糕得多的,這只是比較簡單的一個。」


令應對COVID-19伴隨的嚴重譫妄症變得更困難的是,在病人試圖回到現實的過程中,家人不能陪伴在病牀前。嚴重的病人蘇醒時看見的是一個到處是閃燈和機器的世界,一個睡眠紊亂、醫院人員都穿上防護服的世界。
「這對病人來說影響是巨大的,」曼徹斯特大區索爾福德皇家醫院(Salford Royal Hospital in Greater Manchester)的康復醫學顧問克里斯蒂娜·沃爾頓(Krystyna Walton)解釋說,「他們本來已經很迷糊了,所以這肯定是極其艱難的。」
「如果某個人是患腦炎,有記憶或者覺察障礙,他們沒有意識到冠狀病毒病已經怎樣影響了全世界,於是就無法理解為什麼沒有人來看望。」
全球大流行之下的社交隔離也影響了朋友和家人的聯繫。
西蒙的妻子漢娜·法瑞爾(Hannah Farrell)是丈夫入住的伯明翰伊麗莎白女皇醫院一名神經物理治療師。她記得有一個晚上,西蒙仍然處在嚴重的譫妄症當中時,她認識的一名護士打電話來說,讓她在電話裏讓西蒙聽聽她的聲音,這或許能讓丈夫平靜下來。
「結果,這安撫了西蒙,但是卻肯定沒能安撫我,」她說,「我一整晚沒有睡,因為西蒙聽起來一點都不像西蒙。」
「對我來說,那是挺令人傷心的,而我肯定其他的親屬也說過這樣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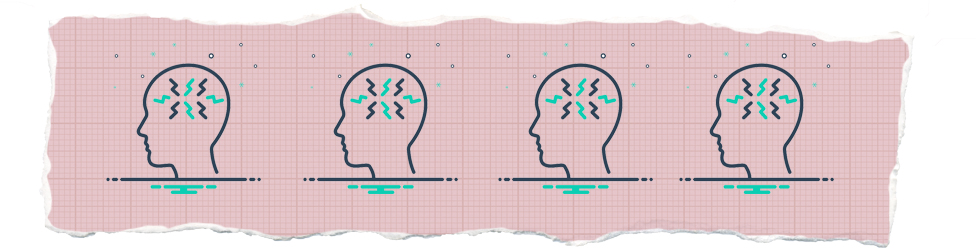
有些病人在蘇醒幾個星期之後仍然會有譫妄症。
凱特·坦塔姆說,在經歷過ICU的病人當中,譫妄症加上其他嚇人的前期感受,「與創傷後壓力紊亂症(PTSD)、焦慮以及抑鬱有重大關聯」。
在平常情況下,經過過ICU的病人當中,大約每五個會有一個呈現出PTSD;而現在的跡象是,在冠狀病毒病人當中,這個數字要高出相當多。
在出院後出現較輕度焦慮和抑鬱的數字也有相同的趨勢。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之下的極端狀況,以及由此而來的社交隔離,很可能令事情變得更糟糕。
例如,在病人離開重症部門轉到療養和康復科之後,缺乏家人令人安心的陪伴仍然是一個問題。很多醫院增設了iPad平板電腦來方便聯繫,家人的聯絡團隊確保視頻通話會每天進行,但這還是不太一樣。

克里斯蒂娜·沃爾頓舉了一個例子:她那裏的一個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病人同時出現了腎衰竭並且做過透析。
病人在重症病房裏度過了好幾個星期,又在另一個醫療部門裏度過另外幾個星期,之後帶著認知障礙被轉到康復病房。
通常來說,在康復病房,工作人員會試圖讓病人周邊的環境變得個人化一些,並且鼓勵他們穿自己的衣服;但是冠狀病毒病疫情的限制令很多這些事情難以做到。
而且由於家人不能探望或者與醫護人員面對面交流,他們經常會苦於不知道他們的親人到底病得有多嚴重。
「在護理院裏沒有訪客,在國民保健署或者獨立機構裏沒有訪客,」沃爾頓說。
「甚至在離開康復科之後,還有一些我們所有人都要面對的限制,使得去一個病弱的人家裏探望也比較難。所有這些都有很大的心理衝擊。」
於是,國民保健署將不得不為可能出現的新一批PTSD病人做好凖備,與此同時還有在疫情最嚴重期間被暫時忽視的一批精神健康及其他類型病者。
「我們會要幾個月的時間才會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大,」多樂茜·韋德說。
「首先,人們離開醫院是松了一大口氣,特別是在住院一段長時間之後。有時候他們可能要頗長一段時間才會意識到,原來有些事情仍然不太對勁。」
事情也不是一定會那樣發展。除了創後壓力之外,醫院也肯定了一個叫創後成長的概念,指出有些病人從重症護理病房出來之後,會對人生有一個全新的看法。
「有一些人——不管情況曾經有多壞——會發現自己處在一個更積極的思維模式當中,」卡的夫重症監護病房的駐院臨牀心理學家朱莉·海菲爾德(Julie Highfield)說。
「人們覺得,這是一個他們從沒想過會有的機會,於是他們決心要活得很好。」
西蒙·法瑞爾肯定是試著將注意力集中在正面的事情上,他的情況一周比一周好。不過,他承認這必須要立足於現實。
「我想人如果覺得身體變好了,他們的精神就會變好,然後就安好了;可是事情並不總是這樣。這兩者是沒有關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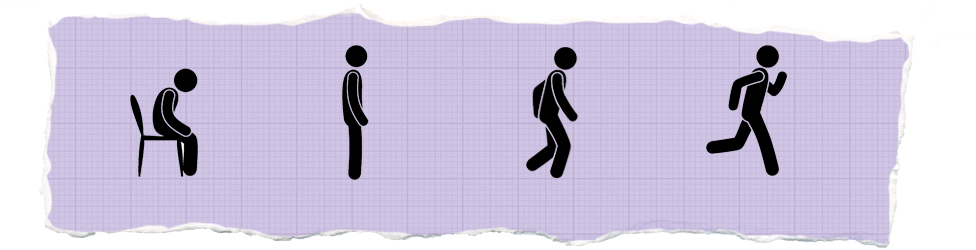
對於很多人來說,身體恢復可能是最大的挑戰,特別是當他們在重症監護室裏度過了很多星期之後。
「冠狀病毒病是一個非常、非常惡毒的病,攻擊你頸脖裏的每一個系統,」坦塔姆說。
有時候當人們像數以千計的COVID-19病人一樣從四個星期的鎮靜劑中醒過來之後,他們唯一能動的就是手指頭。
「我們得和他們一起重建每一個位置,」她說,「並且重新教他們如何做身體的每一個動作——從自己吃飯到摸自己的頭髮,再到站和坐。」
從重病監護病房出來之後面對漫長的康復期並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但是很多COVID-19的病人卻經受特別嚴重的疲勞和肌肉流失。他們精疲力竭——在椅子上坐半個小時之後可能要睡上四個小時,而重建肌肉需要時間。

「如果我們不給病人適當強度的營養攝入,他們就沒法恢復,」坦塔姆說。
於是,營養師的角色就特別重要,還有物理治療師、講話及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如果你剛剛從一個以多種試攻擊身體多個部位的多系統疾病當中痊癒過來,那你需要多種形式的協助才能恢復就是很正常的事。
很多冠狀病毒病人會相對快地回歸正常生活,但是有些人會遭受腎衰竭,可能需要持續的透析,而有些人則需要轉介到心臟科,又或者出現神經性的問題,需要專科治療。
卡爾·瓦爾德曼說,這裏的難點是「要確保每個人都得到所需的支持,而對的支持要在適當的時間到位。」
「我想最大的負擔是在社區,」克里斯蒂娜·沃爾頓說,「因為很多這些病人會有一些比較輕微的障礙,要到回家之後幾星期甚至幾個月,他們的體力開始恢復之後才顯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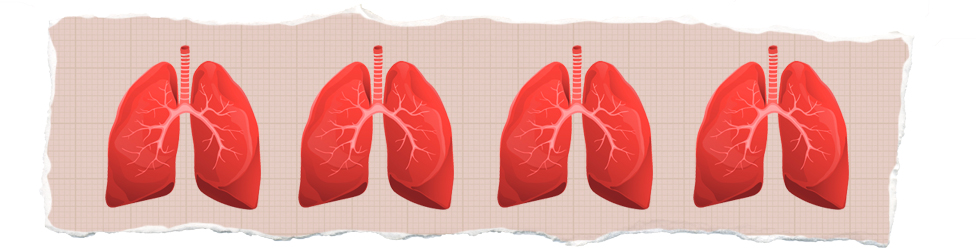
恢復中的COVID-19病人最常見的身體症狀就是呼吸短促——而這是輕微和嚴重症狀的病人都可能有的。
薩麗·辛格說,「出院的病人呼吸急促,很明顯是因為他們有過呼吸道疾病。他們的肺是短暫受損,但是他們身體機能變弱也可能是因為躺在醫院病牀上太久了,身體狀況不佳。」
這意味著上下台階這樣的事情也可能變得極度困難,特別是年長的病人。
但是呼吸急促這個問題會在病人離開重症監護病房之後仍然持續很長時間,而且感染過新冠病毒的絶大部分人仍然難於擺脫。
珍妮·戈布拉特(Jenny Goldblatt)是皇家自由醫院的一名感染科醫生,在3月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而此後各種後遺症狀就沒離開過——一輪接一輪的身體疲勞、胸疼和呼吸困難。
她3月在醫院住了兩天,在那裏接受了一些額外的供氧,但是在回到家之後,她的問題才全面顯現出來。
「每10天左右我就會開始感覺好一點,然後就開始做長一點的散步,」她說,「然後我就會一頭扎進被窩裏,一個星期都起不來。」
患病之後的一個月,她才第一次能夠走到一條路的盡頭再走回來。作為一個自行車愛好者,她的下一個目標是圍著街區騎一圈。
「我無法想象,我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地騎行,而如果我想太多的時候,這就有點令人憂鬱。」
珍妮認為她的病毒已經清除了,而且她血液有「輕易檢測得到的」抗體,但是她的身體還是繼續出現不尋常的反應。病後的疲勞並不是COVID-19才有的,但是這不止這麼簡單。
珍妮還有胸疼和呼吸急促;其他病人報告的後遺症包括嚴重頭痛或者腹痛。生病之後三個月回到工作崗位或者恢復正常生活是不可能的。
「我在慢慢地好轉,」她說,「但是我不能太期望。坐上這架過山車很令人沮喪,對這段路要走多久完全沒有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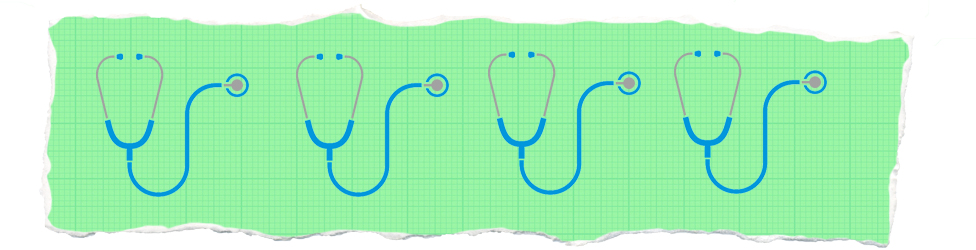
過去關於肺炎的經驗顯示,這可能要花好多個月,一些極端案例甚至要好幾年,病人才能回到之前的狀態。對於COVID-19,我們還處在康復週期的很早階段,而且每個病人的情況都不一樣。
「坦白地說,我們還不知道它會需要多長,」薩麗·辛格說,「我們一邊說的時候,人們已經在研究——監察胸透X光、症狀以及病人的情況,來幫助我們找到支持這些人的最好方法是什麼。」
麻煩的是,全英國各地提供的康復服務可能參差不齊,特別是對重症監護室出來的病人。國民保健署已經在處理一大批滯後的非新冠病人。
克里斯蒂娜·沃爾頓說:「巨大的挑戰將會是數字的上升。」
在爆發的最高峰時期,首要任務就是要讓病人盡快脫離危急情況,以空出醫院牀位。這意味著,在很多時候,通常要在醫院裏進行的康復評估都改成在社區、療養院或者非特設的康復環境裏進行。

「而我的懷疑是,」沃爾頓說,「很多病人的需要可能並沒有得到恰當的評估。」
致力於改善重症患者康復情況已經25年的卡爾·瓦爾德曼說,他能想到的最好比喻是就像在造火箭,培養太空人。
「你將他們送上太空,但是你要考慮他們要在哪裏著陸,以及他們回來之後我們要做什麼。」
他說,你將一個病人送到重症監護室裏經歷那一切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我們有一些病人,需要七個專項人員來照顧,」他說,「而且除非他們湊齊這所有的拼圖,否則他們有機會完成不了應有的康復。」
要強調的是,這些康復的需求不會在初期的康復期過去後就停止。很多病人會遭受肺纖維化——一種永久性而且常常是傷害機能的狀況。醫生還知道,相當數量的重症病人會遭遇認識障礙。理想來說,他們是應該經過篩查,才能重新開車或者回到工作崗位。
「康復過程必須某種程度上融入到現實生活並且回到社區,」克里斯蒂娜·沃爾頓說,「做你之前做的事,照顧你的家人,獲得收入,享用休閒設施和做運動。」
「而這是需要時間和專業知識的。」
當然,國民保健署和獨立醫院是將康復納入了他們的冠狀病毒病恢復計劃裏了,但是這個系統已經被忽視多年。該領域的專家希望,雖然面臨如此多的壓力,冠狀病毒病將會帶來一種改變的動力。
「醫院在治療病人、對人採取手段使他們好轉等方面是非常好的,」凱特·坦塔姆說,「但是他們並不總是做得很好的事情是,將事後的療癒和康復事務納入重要程序。」
換句話說,這不僅僅是關於生存,而且是關於與健康有關的生活品質。
「讓某個人經歷重大的重症治療之後,如果你不試圖讓他們回到他們想去的地方,那就沒什麼意義。」
*參與報道:奧利弗·巴恩斯( Oliver Barnes)
*插畫:艾瑪·林奇(Emma Lynch)